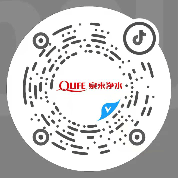情感与理性是天然生成的一对对立,关于一般思想是破坏性的东西,关于诙谐感则可能是建设性的成分。
有这样一段对话:教师:“今日咱们来教减法。比如说,假如你哥哥有5个苹果,你从他那儿拿走3个,成果怎样?”孩子:“成果嘛,成果他肯定会揍我一顿。”关于数学来说这完全是愚笨的,由于掉包了概念。
教师讲的“成果怎样”的意义很明显是指还剩下多少的意思,归于数量联系的领域,但是孩子却把它搬运到未经哥哥答应拿走了他的苹果的人事联系上去。

但是关于诙谐感的构成来说,好就好在对这样的概念默默地搬运或掉包。仔细分析一下就可发现这段对话的设计者的匠心。他本能够让教师问还剩下多少,但是“剩下”的概念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很难搬运,所以他改用了意义弹性比较大的“成果”。这就便于孩子把减去的成果悄悄转化为拿苹果的成果。
能够说,这一类诙谐感的构成,其功力就在于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把概念的内在作大幅度的搬运。有一条规则:掉包得越是荫蔽,概念的内在距离越大,诙谐的作用越是激烈。

柏格森在他的《论笑》一书中指出,诙谐是“镶嵌在活东西上的机械的东西”。在瞬息万变的日子中,忽然一个机械呆板的体现当然好笑。在卓别林扮演的喜剧中,使用人物的机械死板体现出的笑话,俯拾即是。
有一个电影体现在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流水线上,一个工人的悉数动作都被扳螺丝钉的动作同化了,以至于他看到女性衣服上的扣子也要当螺丝钉去扳一下,成果笑话百出。